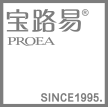廖方:万花筒里看《繁花》 海派空间转“魔方”
日期:2024-02-21作者: 产品中心
不舍昼夜的外白渡桥、文艺复兴风格的外滩27号、装饰艺术派(Art Deco)的和平饭店、十里洋场的南京路、姹紫嫣红的黄河路、弄堂毗连鱼肆排档的进贤路、牯岭路 ——《繁花》开场的方圆三两公里,之于今日上海市域不过一隅之地,却在屏幕内外都犹如万花筒般令人目不暇接。回溯两三甲子,这一系列异质乃至背反的空间类型依次登台汇集,拉开了上海地区从近旁的“古代县城”向此间“近代城市”跃迁的大幕;20世纪90年代,它们又集体亲历着上海第二轮举世瞩目的城市化浪涌,再次幻化出海派空间的迷人魔力。

时间能改变一切,而一切改变都发生在空间之中。在《繁花》呈现年代的同期,世界思想界也正在发生某种“空间的转向”,正如福柯所言,空间不再被当作僵死、刻板、非辩证、静止的东西,而是被看成富有启发和生命力的概念。再度成为全球化“桥头堡”的今日上海,并未陷入通常伴随全球化而来的“千城一面”的空间迷茫,却又因此带来饶有趣味的空间迷思:一座城市的空间何以成就风格,空间风格之于一座城市又有何样的意义?
思想界的空间转向,始于人文学科与地理学科的双向奔赴,而当相关学术观察进入城市内部,以塑造人工空间为核心的建筑学,自然被编织其间,并极大丰富和发展了人文学科的理论架构。如在艺术品领域,建筑具有不一样于其他艺术形式的特质,即不但可以在外部欣赏,还能进入内部体验。建筑的这种人文空间艺术性进而在城市层次同构,建筑群的壳体既是各自内部空间的外围,又共同构成城市空间的内壁。城市由此成为最日常又最宏伟的艺术品,这种日常与宏伟不仅是实体的,更是空间的,因为实质上是空间在承载着各类城市生活,并成为城市生活本身的一部分。同时,由于建筑与城市空间是天然存在于公共领域的大尺度对象,因此也成为无法束之高阁而不得不面对评论的艺术形式。
悠远的世界城市银河中,闪耀着铭刻空间艺术风格的群星:雅典的神庙柱式是西方语境中“秩序”(order)的前身,也是最初供奉城市守护神的卫城(Acropolis)区别于城市其它部分的标志;罗马的巴西利卡成为以市政厅为首的西方世俗公共空间的原型,由此被面向世俗的基督教在合法化后选作公开举办仪式的厅堂;拜占庭的希腊十字教堂和巴黎的拉丁十字教堂在中世纪分别象征着东、西罗马帝国的政教权威,这两者在佛罗伦萨圣母百花堂的结合又成为了文艺复兴的报春花;之后维琴察的一处城市更新项目中诞生的帕拉弟奥母题至今仍是普遍的使用的经典构图模式;20世纪20年代,魏玛包豪斯校舍将“流动空间”抽象为一种设计风格引发轰动;而明清时期的江南,已将类似的空间手法诗意地运用于园林和城市;包豪斯校舍落成前一年,巴黎世博会推出的装饰艺术派,数年间就经美国风靡全球,又于二战后快速沉寂,至90年代再次复兴……
反观上海,上述样式面面俱到,但又都并非源于上海;《繁花》之中的单个场景皆形象鲜明,但又都非上海所独有;如此,海派空间风格,在沉浸之余又从何把握,在意会之外又如何言说呢?其实自文艺复兴时期起,全球范围内的城市空间风格已开始不可逆地摆脱形制化样式的桎梏,难以像古典建筑那样“纯正”和易于“按图索骥”。但城市始终是社会力量投入空间生产的成果,城市的街区建筑形象,勾勒出社会力量对比变化的图景。因此,城市空间“流派”的建构仍然遵循社会力量机理,探究“城市上海”空间生产的动因,是研究者书写海派空间文本的认知基础,也有助读者免于乱花迷眼。
大都市往往都有清晰的中轴线以规制总体格局,如北京、广州、巴黎、华盛顿等,连一江之隔于30年前兴起的浦东新区,也有一条始于陆家嘴迄于世纪公园长达5公里的中轴线,而《繁花》所处的近代上海城区却是例外。进一步观察路网形态,外滩周边的街区尚显方正规整,西进仅约1.5公里越过今西藏路一线后,即变得在工具理性视角下难言合理:一方面许多“填浜筑路”而成的“小马路”蜿蜒交错或起止随意,另一方面诸多干道在远离后仍保持与外滩岸线基本垂直的走势却与正南北朝向有较大偏转。再进一步比对近代上海不同时期的地图能够准确的看出,城区范围快速扩张的同时却长期延续着极为罕见的“一城多府”治理格局和大片游离于华界租界之外的“越界筑路区”。
近代上海独特的城市化进程,衍生出如魔方般多面多彩的空间气质。老城厢及南市很大程度上仍保留着江南水乡的空间尺度和肌理;公共租界的中央区和西区(原英租界)是近代城市上海的起源地和核心部分,其中的外滩至今仍是上海最富盛名的“第一名片”;法租界起步于英租界和老城厢之间,向西延伸至徐家汇,享乐和文艺气氛浓厚;公共租界的北区和东区曾是原美租界,但实际上美国人一直并不多,大部分区域被日本人长期占据,氛围明显相对内敛;相较于各自为政的华界或租界,越界筑路区则牵扯着更复杂深刻的中外政治力量博弈、中西文化迎拒、民族心理抵牾,是为最奇葩者。
随着上述五大类空间扩散渗透,加之法理之外的越界筑路多为仓促之举,以及经历了西方建筑学的逐步登陆和建筑潮流从新古典主义向装饰艺术派的总体转向,近代上海这只极其独特的都市“魔方”不断翻转,每一面都演化为驳杂跃动的马赛克拼花,并从超视距的宏观大片区层次,向目力所及的中观街区层次同构,但又难以在孤立的单体建筑上直接体现。因此,“街区”成为最适合“人”直观体验海派城市空间特质的对象,是“建筑阅读”的“上下文”。更耐人寻味者,一是空间魔方变幻活络又紧密嵌固,混搭相处又各自“拎的清”;二是空间风貌的多样化往往并非源于业主或建筑师的故土,许多身处上海的外侨们在置业时选择了各种“第三地”的样式,如《繁花》中的外滩27号与和平饭店,分别由英商怡和洋行、维克多·沙逊投资,英商思九生洋行、公和洋行设计,但皆未采用传统的英式风格或中式风格,而是选择了源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风格与源于法国盛行于纽约的摩天大楼装饰艺术派,“爷叔”为“宝总”挑选的“英国套房”,也只是楼内众多房型中的一种。
相对窄小亲切的尺度,蜿蜒变化的线形,于“路”而言不是最优,于“街”而言则常常为活力与趣味所倚。同时,近代街区的市政体系具有架构稳定性,不易大举颠覆,而源于戏剧化的近代空间生产的“马赛克式”街区,又能最大限度地兼容不同时期的空间再生产。只要路网框架形态存续,内部建筑单体乃至街坊的置换都不会导致街区“转基因”。实践也表明即使再次经历了城市高速建设阶段,建筑物“平均身材”大幅度的增加,但海派街区的总体“质感”并未被涂盖并得以焕新,因其本身就是新陈代谢的生态系统而非僵化的舞台标本。
年底热映的《繁花》与年初热销的 City Walk,仿佛两只蝴蝶飞进上海的窗口,上海当前也确实处于新一轮城市更新的时间窗口。不可否认,这两种“都市品”都是舶来品,但都是上海对标的全世界城市的舶来品,蕴含着深刻的规律启示。那就是在城市已成为国际竞争主角的当代,城市品牌是竞争力的核心部分。
如果说上海地区在近代时期的初始城市化主要源于地缘条件,那么30年前上海再次逐浪潮头的背后,相信很大程度上已有城市品牌效应的考虑。回顾时空,面对总体产能过剩的全球市场,城市乃至国家品牌的塑造早已风生水起。前文提及的包豪斯,源于1917年成立致力于提升“德国制造”竞争力的德意志制造联盟;感受到德国压力的法国,克服一战后的困顿于1925年举办巴黎世博会催生装饰艺术派风格,包括老佛爷在内的巴黎四大老牌百货公司都设计了新颖的展馆;艺术装饰派进入美国后迅速衍生出芝加哥、纽约、迈阿密、好莱坞等多地的流派;70年代伦敦兴起 London Walks,城市空间进一步“润物无声”;之后电视网络及互联网的兴起,又为城市品牌提供了新的虚拟空间载体。
上述种种的城市品牌活动,也都发生在空间之中,或以空间为素材,因为城市的本质就是容纳和激发城市生活的空间。从雅典的卫城到罗马的广场,从威尼斯的水城到圣托里尼的天街,从巴塞罗那的棋盘网格到巴黎的放射路网,戏剧化的空间本身就是最可沉浸体验城市品牌的场域。但戏剧化的城市空间又像妙手偶得的文章难以复刻。上海的发展道路是独特的,上海就是上海;上海因此也是幸运的,自带可遇不可求的空间魔方。深刻的城市更新,基于深刻的城市规律认知;把握城市更新,始于把握可遇不可求的城市空间风格。以海派空间风格彰显海派城市品格,以海派城市品格塑造海派城市品牌,这是值得深思的时代命题。(廖方)